一場街頭藝術之社會實驗

明目張膽的偷狼事件 是Banksy精心安排?
近日,倫敦各地接連出現來自著名英國街頭藝術家 @banksy 的新作,迅速成為了城中熱話。由第一天一隻危立在Kew Bridge的山羊開始(已被封存保護),到第二天位於Chelsea窗上兩隻遙望的大象,再到第三天在Brick Lane鐵路橋上掛著三隻猴子,這些作品逐日出現。當中第四天最為轟動,因為在Peckham一隻畫在衛星碟型天線上咆哮的狼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火速偷去。接下來第五天,是兩隻在Walthamstow一間炸魚薯條店外正在吃魚的塘鵝,第六天則有一隻畫在Cricklewood一塊舊廣告牌上的正在伸懶腰的野貓(數小時後被拆去)。第七天倫敦市中心City of London金融區,一個警察崗亭被變成魚缸,裡面充滿食人鯧(已被移去)。第八天的作品於Charlton有一隻趴在一輛廢車上的犀牛(車子隨後被移去)。在我撰寫此文當日,倫敦動物園門外出現了一隻大猩猩,正在嘗試釋放其他動物,這是第九天的作品。目前尚未清楚這個以動物為主題的系列會於何時結束?亦不知道這些作品會有什麼下場?但毫無疑問的是,每一件作品都已成為新聞焦點。


一場考驗人類本性的社會實驗!
目前尚未清楚這個以動物為主題的系列會於何時結束?亦不知道這些作品會有甚麼下場?
Banksy深知他的作品可能會被人拆除或偷走,進而進入藝術市場牟利。這種現象已成為他作品的一部份,揭示了人類的貪婪與自私。每次他的作品現身,就如同一次社會實驗。


每天有數萬人踏過的藝術品?
有些街頭藝術確實喧鬧,經常以高姿態去吸引眾人眼球。轉往另一邊廂,也有人無聲無息,默默地在街頭持續創作。不知你有沒有留意到,位於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對開那條每天有數萬人經過的千禧橋(Millennium Bridge)上,竟然隱藏著大量微型畫作?
這些作品極度細小,很難被來去匆匆的人們發現,因為它們極度細小,那是一幅又一幅畫在香口膠漬上的作品,出自英國街頭藝術家班·威爾遜(Ben Wilson)之手,他亦因此獲得了「香口膠人」(Chewing Gum Man)的稱號。Ben Wilson從2004年開始這種非傳統的藝術形式,將街道上的香口膠漬變為色彩繽紛的小型藝術。他在千禧橋上創作了數百幅迷你畫作,從抽象設計到人物、動物和世界各地不同的場景,應有盡有,你甚至會發現以香港為題材的作品!
Ben Wilson的藝術既是一種創作,也是一種關於城市廢棄物和公共空間的聲明。香口膠漬原為令人討厭,被視為垃圾的城市污漬,而他卻將其化為創作的機會。他的作品不僅美化了公共空間,也挑戰了傳統藝術的概念,因為他的畫布正是一向被人視為垃圾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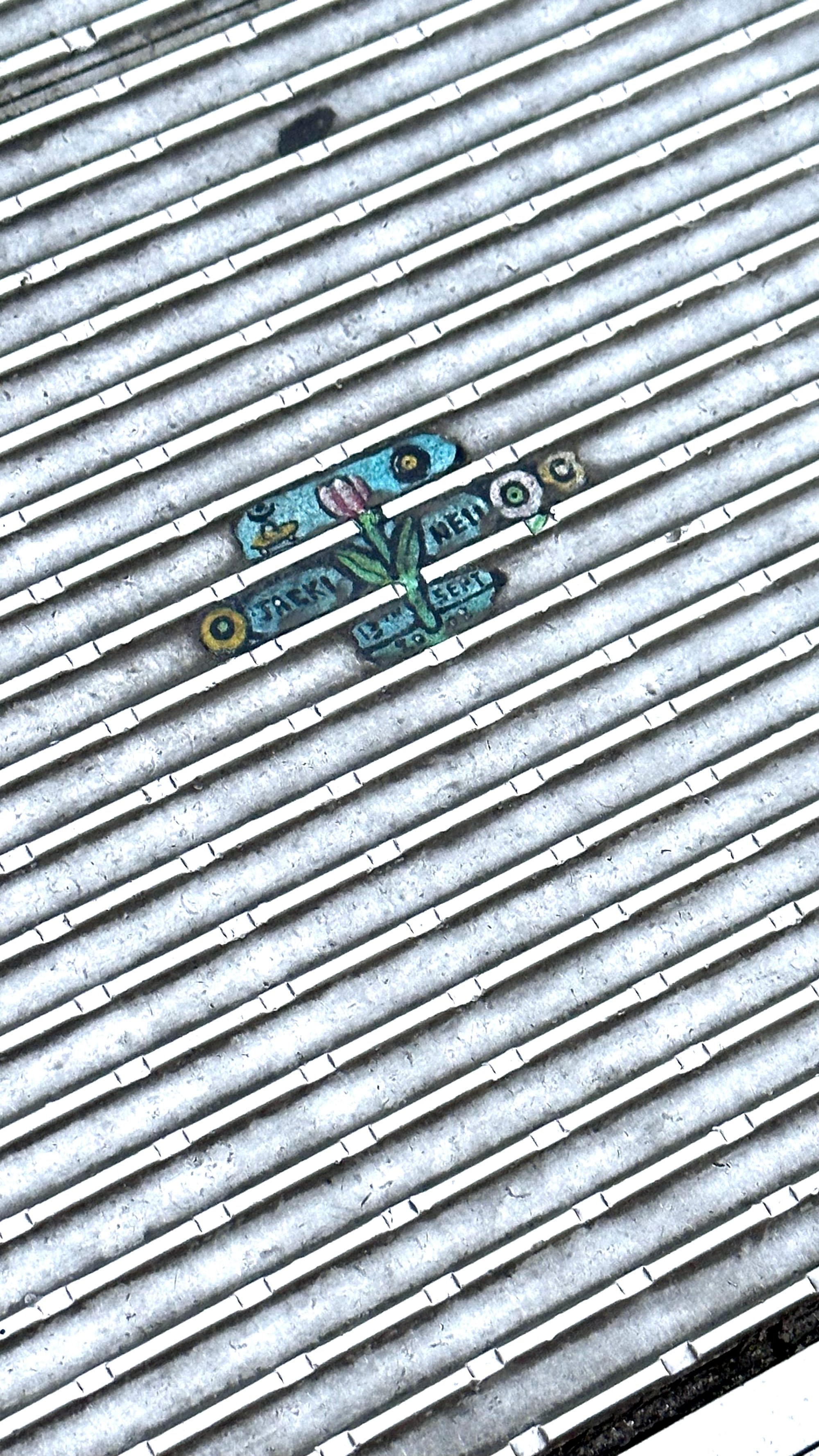


即使早前部份作品因為倫敦清潔隊的例行清潔而被洗去,Ben Wilson仍然繼續創作。靜靜地伏在橋上作畫,一天又一天,持之以恆。
微小的香口膠藝術宣言
在殿堂級的泰特現代美術館前,這些微小的藝術品顯得尤其有趣。它們不屬於任何藝術市場,也沒有藝術金字塔頂的光環。Ben Wilson只是靜靜地伏在橋上作畫,日復一日,並持之以恆。即使早前部分作品因為倫敦清潔隊的例行清潔而被洗去,他仍然繼續創作。每次踏在千禧橋上,我都會因這些微小而美麗的作品而會心微笑。有次甚至有幸偶遇本尊,並告訴他我非常喜愛他的作品。他的創作為千禧橋注入了生命力,因為這些畫作會不斷更替,一期一會。它彷彿用以告訴繁忙的城市人,叫他們嘗試停下腳步去多一點細看身邊的事物。原來日常生活中,很多有趣的東西就在我們身邊,只是我們沒有發現。
無論是「香口膠人」Ben Wilson的作品還是Banksy的創作,它們都是與周邊環境緊密相連的「Site-specific Art」,其所在地及周邊的細節,都是作品的重要部份。當這些作品被移至其他地方,作品的內容與脈絡便會隨之消失,變得毫無意義,剩下的只是一張「Banksy的作品」。Banksy自然深知他的作品很大機會會拆除甚至偷走,繼而進入藝術市場銷售牟利。這種現象現已成為他的作品的一部分,好像要揭示人類的貪婪與自私,每次他的作品現身,就如同一次社會實驗。
如果你對攝影運鏡稍有了解,你或許會注意到那次在Peckham明目張膽的偷狼事件,全程竟以手持攝影的方式近距離拍攝下來。有人猜測這是Banksy精心安排的setup,目前尚無法確定真相。


____________________
Rachel IP 葉曉燕
視覺藝術家、藝術教育工作者、策展人、藝術專欄作者。以攝影研究及藝術史為主。在大學任教十年,現居倫敦,繼續在網上推廣藝術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