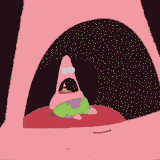無美男同志故事 卻成為電影天花板《漂亮朋友》是甚麼電影?

耿軍來過香港數次參加影展,每次都只是留一兩天、走馬看花。今次隨《漂亮朋友》在亞洲電影節上映,可以留在香港多數天,或許有機會找城市規劃的朋友到處走走。
「香港物價真的很貴。」唯獨這多年的印象在耿軍中揮之不去。

《漂亮朋友》的故事埋藏於耿軍心中二十多年,他說有位比他大十來歲的大哥中年出櫃,在二千年代時某個飯局向某人示好,後來被對方拒絕及打傷,於是離開了東北,從此便失去聯絡。

直到2020年疫情來到,世界各地也隔絕了社交,眼神變得閃避,手不能握,更不用說擁抱,東北地區亦不例外。「那時,人跟人之間溝通見面日常生活全都非常艱難,同性愛情在我們那個環境裏邊也很艱難。」故事寫在疫情時,但戲內卻是疫情前,將那社交距離,變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當時感覺世界末日來了。我想,是不是應該寫個純愛電影,在低落時來點歡樂。」於是便按此為原型,叫各演員觀察身邊的同性戀者並寫下故事。可是,即使是兄弟班也是會已讀不回。

耿說最初向幾位演員說要拍同性戀的電影時,他們都笑著不相信,可是笑著笑著便拍了。「40歲加或者45歲加這個年齡段做愛情電影,這件事是日常裏面不太容易想象的,我們看電影的時候就是這個年齡段的愛情不多,所以他們一開始不相信。」一班中年男人要赤裸演出,沒有信任是拍不了。「在二十年前拍短片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怎麼導,他們(演員)也不知道怎麼演,我們就在這種懵懂懵懂的時候就開始創作短片。」演員更是中途出家,在耿軍第一部短片作品《錘子鐮刀都休息》之前,張志勇當過的士司機及煤炭工人,徐軍當過教師,也只是靈光一閃齊齊拍片,一下子與耿軍一起合作二十年。

電影故事講述東北邊陲小鎮,兩位中佬擦出愛火花,而同時兩位女同志更借精產子。戲內男演員徐剛、張志勇及薛寶鶴外表不揚,不像一如以往同志電影的美男交女,又或是泰劇那般賞心悅目。在《漂》的三人表現是光陸怪離,薛寶鶴的大肚腩赤裸強吻演出,說成是「痴漢」也不為過,然而他們並不惹人討厭,反倒是會心微笑,荒誕中帶點黑色幽默,所以被譽「華語同志電影地板跟天花板」。
「我近十年的電影,其實都是按着他們自己的名字來寫作的,但是在剛開始給他們劇本的時候,我會跟他們說跟你想的一樣,我說張志勇有可能演薛寶鶴,薛寶鶴有可能演徐剛,徐剛有可能演張志勇。雖然我用了你們的真名,但是他們就非常自覺的熟悉整個劇本。」
剛過去的金馬獎,香港有份角逐最佳男主角,可惜在最後一輪敗了給《漂亮朋友》,由張志勇奪得,然而這位影帝一直對自己的外表有芥蒂。導演耿軍跟張志勇自小便是朋友,他說張某次在礦區拾到爆破雷管,便帶回家後嘗試拆除,殊知走火爆破,令眼睛手指受傷,雖然康復了,但留下傷痕,所以最初拍攝時沒有太大信心,甚至會避鏡頭,經了一番努力才克服。「他們現在已經是非常棒的演員,別人管他們叫老師的時候也不用心虛了。而如果有人說他在表演上已經是藝術家,我覺得這樣的褒獎我希望他能接得住,這就是你接下來要繼續創作好的人物。」

雖然會惱火兄弟的愛理不理,但有種默契放於心中。「沒有他們便拍不了,是非常難的。」電影的黑白片模式並非耿軍最初主意,是攝影王維華在讀了劇本下反問導演,他認為要拍薛寶鶴的身形,要有一種雕塑感覺用黑白片影形式拍會更立體,於是電影便這樣去了,也由這種默契拿下金馬的最佳攝影。
香港電影走入瓶頸,合拍片少了,本地製作變多了「獅子山下」,甚至被網民說成是慘情戲,而大師如杜琪峯導演也要先中途暫停,要處理好自己思緒及對香港的感覺才能拍下去,在一片灰濛中沒有答案。
東北鶴崗淒淒慘慘的荒涼景色,一直是耿軍鏡頭下的取材地,也是他成長的地方。
「童年、少年、青年都是在我的家鄉度過的,那是我的一個樂園,在那兒拍攝特別有安全感,遇到什麼問題打個電話就能解決掉。」
這個小鎮原先是煤城,礦坑隨處可見,後來因時代變遷而陶空了城市,鳥不生蛋。「我自己家住在郊區平房,走五分鍾就是菜地,走半小時就是百貨大樓,但同時它又是煤礦的塌陷區不適合居住,包括我們上的中學都被拆掉了,所以在2013年拍了《錘子鐮刀都休息》都是爲了把熟知的地方在影像裏留下來,拍了熟知有情感的那些區域。」

然而,這樣的地方給成造了他。「東北人是天生有幽默感。」既然世界已這麼荒誕,也只能笑著面對。
戲內張志勇及徐軍彼此拉近又挑逗,徐軍要對方猜底褲顏色,張志勇在床上吐口水及求掌摑的場面,而第三者薛寶鶴又無限熱情介入,三人化學作用令人感覺到無比荒誕,最後更有外星人的機械降神,愛情故事中就是有無限可能。「人跟人之間最重要是溝通,情感又會有隱祕的部分,就有的時候我也這樣會會心一笑。」
電影涉及同性議題,也不會在中國上得了畫,而台灣也各種問題難以放映,在香港的電影節播放時,難怪一窩蜂說普通話的人圍著演員索取簽名。他說自己的作品只是情感的電影,其他工作管不了,作品被修正,他有經驗。
最標誌就是《東北虎》其中一句「喝完就他媽離開這個操蛋的世界」,被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指不可以這樣說。「有十四個月的審查中期,有七八次修改意見有十四個,每一次修改意見都非常讓人惱怒,但你又不知道是誰提的,我們能做的很有限,拍完後台詞被改了,又怎可以補拍呢?誰出錢呢。」他續說:「我不是一個受迫害妄想症的一個人,電影而已、藝術而已;電影有電影的自由、藝術有藝術的自由、商業有商業的自由,這樣才是一個好的社會。」面對創作,他能夠做到的是不先自限想像,盡量能讓自己自由一些,假設一切一切都不會出現。

互相理解是不少作品展現世界的理想「這力量是很微妙的,能互相理解一點,能達成一個溝通。」他也夢想著。
電影交由法國公司處理,自己亦是首次看到電影有周邊。「不單單在熒幕上,也能在生活上陪伴大家,面對觀衆或者影迷的時候,我不知道對他們說什麼,因爲我想要表達的,想跟他們溝通的在電影裏面完成了。」唯獨一句。
「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是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