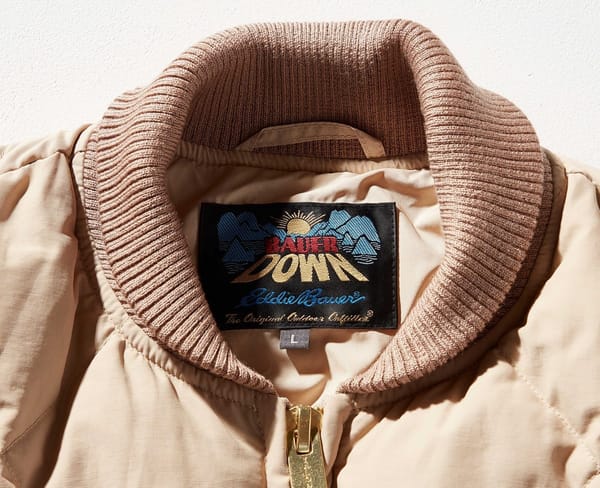香港建築界傳奇專書上架!

本地建築師兼建築歷史學者黎雋維花了足足7年時間梳理建築師何弢(1936-2019)留下的圖紙、筆記等,最近整理成新書《重遇:何弢——香港建築師的跨界宏圖》。為何要這樣花心力?他表示這不僅是對建築大師的致敬,更是一次重新發現香港城市願景的過程,深思城市的潛能。你知道何弢為香港留下了甚麼嗎?

#01 文化沙漠煲無米粥 | 香港藝術中心(1977)
在香港藝術資源匱乏的70年代,何弢與白懿禮、盧景文等倡議成立一座民間藝術中心。最終政府只願撥出灣仔一塊三角形小地皮,何弢便巧妙地以三角形為主軸設計結構,將不同樓層連結成開放式的垂直空間。他希望建築能夠在香港這個所謂「文化沙漠」中也可以「煲出無米粥」,「『無米粥』希望對香港、對藝術文化有興趣的人,是一種刺激。」


#02 香港建築代表作? | 聖士提反書院科藝樓(1980)
這可說是香港粗獷主義(Brutalism)的代表作,是首批獲德國SOS Brutalism組織認證的香港粗獷建築。不加修飾的清水混凝土牆面與外露的結構,展現出雕塑般的魅力。為了不讓建築壓迫周遭環境,何弢特意將立面設計成往後縮的斜面,層層退讓,與山坡地形完美結合。粗獷不等於粗糙,反而是一種誠實的建築語言。


#03 工業也可以優雅 | 港鐵臨時辦公室(1976)/ 荃灣車廠(1982)
據黎雋維表示,建築師嚴迅奇說過何弢早期為港鐵設計的寫字樓令他留下深刻印象。何弢於70年代為港島綫地盤設計的臨時辦公室,回應當時提倡的高技派(High-Tech)思潮而於將粉色通風管不加修飾地外露於人前,成為亮眼的視覺焦點。那邊廂,他為荃灣車廠設計了多款裝飾模板,令佔地廣闊的車廠展現出一份莊重和秩序美。


#04 樂富驚喜地標 |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2000)
這幢如飄浮於半空中的建築結合立方、長方、球體兼三角等幾何,結構複雜到不得了。面對地基僅約1,500平方米的限制,何弢將禮堂、辦公空間等垂直疊合;並刻意將聖堂置於底層以方便舉辦婚禮等儀式,更親自設計彩繪玻璃讓自然光從側面柔和滲入室內;至於教堂標誌的三角則以通空設計置於建築最高點,展現出另類氣派。


#05 旋轉動感是關鍵? | 香港區旗(1990年代)
除了公共建築,何弢曾獲香港總督彭定康邀請裝修港督府。至90年代,他更受邀設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與區徽。他認為洋紫荊花瓣的排列帶有旋轉動感,藉此反映香港社會的動感和活力。他手畫過無數草圖後,最後成為了一眼便能認出的香港象徽標誌。



何弢以香港作為實驗地
何弢絕對是有料之人,於美國留學期間師從Le Corbusier門生Josep Lluís Sert及建築評論家Sigfried Giedion,回港執業前更曾任現代建築之父Walter Gropius助手,接受嚴格的包豪斯訓練。1964年返港後,於1968年開設自己的事務所。70年代正值是香港經濟及建築業起飛、城市擴展的年代,讓他有機會將理論學以致用,為香港帶來一場現代建築革命。

不買政府帳!最敢言的建築師
何弢不僅是建築師,更是一名尖銳的觀察者。他於90年代公開以「娘氣」批評香港中央圖書館的設計,大膽表示不論不類,絕不買政府帳。此舉引起一番熱論,而何弢堅持批評和評論對於建築設計非常重要,否則建築師就會成為「自戀狂」。說到底,公共建築就是要向社會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