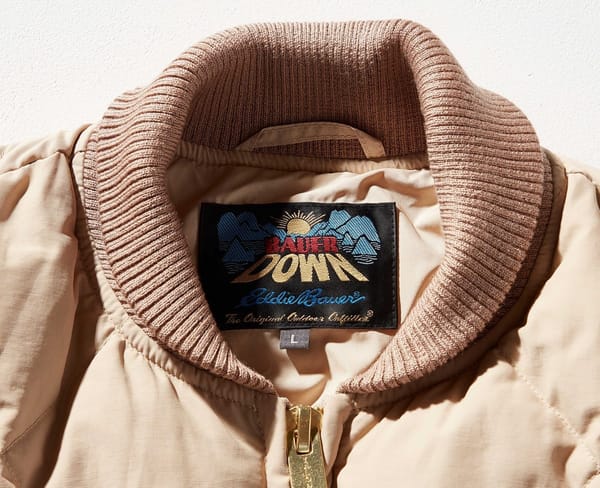消失中的香港風景(一)本地霓虹燈招牌兩年間被拆除3,500個 「街招」如何拯救舊招牌?

◎text_emily | ◎photo_SIU FAI、@modernismhongkong |
招牌是建構城市風景的關鍵元素,是城市美學的重要象徵。曾幾何時香港街道掛滿了大大小小的手寫書法招牌與霓虹燈招牌,為城市景觀注入靈魂,可惜近幾年不少吊掛於半空中的招牌因建築物條例而無奈被拆。由馮達煒(Ken)及麥憬淮(Kevin)兩位建築師創立的「街招」,便以自己的方式著意保留快要一點一點失去的香港美學。

從建築師到成立「街招」:Ken與Kevin的保育之路
在2022年11月尖沙咀天星碼頭的一間地舖內,放滿了模樣各異的招牌。九龍城公和荳品廠、和昌大押、海安㗎啡室、沙龍洋服、文華冰廳、廣同安藥行……如此近距離細看實在震撼。這是Ken及Kevin所創立的「街招」努力保留被拆卸的舊招牌,更為它們存檔—招牌物料、出現年份、清拆原因等等,將香港街頭美學有系統地整理歸納、好好保存下來。

份屬中文大學建築系的同學,兩人在畢業後碰巧在同一公司工作,沒料到這段緣份竟一直延續下去。這個轉捩點要回溯至2015年,「記得我們有天一起吃午餐,偶遇到一家押舖正在清拆招牌,那隻字很美,因而問工人能否讓我們保存下來。那時我們還未深入探究香港招牌文化美學,純粹不希望城市裡如此美麗的事物就這樣在堆填區裡消失,因而第一次拯救招牌。」
就這樣他們漸漸開始留意得到香港招牌消失得愈來愈快,但沒有甚麼確切的行動。「至2017年我們參加了一個設計比賽,初嘗試借用舊招牌去講社區的故事、談歷史文化,發現原來會有人留意,就此我們在社交平台開設了專頁『街招』去深入分享香港招牌的故事。」他們除了鼓勵店舖傳承招牌街景外,在專頁簡介裡還這樣寫著:以推動實現招牌街景成為都市文化遺產為目標。

保育香港霓虹風景 提高公眾關注度
過去五年間他們為了實踐這個目標而全力進行保育的工作,「一開始我們希望可以運用自身對建築物條例的認識及專業背景,為收到清拆令的店主提供資詢,盡量嘗試原址保育。可是因現行條例所限,絕大部份招牌最後都需拆除,而拯救這些拆掉的招牌就變成一個折衷的保育方案。」
拯救之後並不等於就此了事,「我們不希望這些招牌從此就放入倉庫,因此透過不同的展覽將這些招牌再次展示於公眾眼前。每個展覽都定下不同的主題,藉此展示招牌背後的不同價值—店舖、行業、社區歷史、招牌物料工藝、書法、設計等,或跟其他不同背景的單位合作,希望提高公眾對招牌保育和關注現行條例中的不足。」近來便先後在上文提到的天星碼頭帶來「招牌種子庫」及中環PMQ帶來「在十七天後」兩個展覽,前者展示招牌美學而後者則引導大家反思招牌去留的評審標準。成立後的五年間已拯救了一百二十間店舖招牌,「起初主要是多走在街上,留意招牌搭棚或店舖張貼結業通告;現在主要是由這五年認識的保育界、文化界朋友及社交平台的Followers轉告消息。」
疫情期間招牌消失速度加快 逾3,500個招牌被拆除
招牌一個又一個在街上拿掉,「早年2010年實施新條例招牌被清折的速度最快,屋宇署會每年定出『重點街道』去出清拆令予整條街道的商戶,在短時間內整條街道的招牌便會被迫清拆。當時整體香港的招牌仍不少,而視招牌為城市文化、文物的概念還未成形,比較當時,現在我們對街上餘下唯一的招牌清拆的警覺性會較高,是文化教育社會環境的觸覺影響。其後疫情影響經營環境以致店舖的結業潮,到最近新一屆政府推出美化市容計劃,2022年拆除一千七百個招牌,2023年拆除一千八百個,都令招牌消失速度加快。」

「現有監管條例對街上原有的招牌採取一刀切的處理,就是視為僭建物,大多以發出清拆令要求店主拆除,以致近年招牌不斷從街上消失。雖然有機制保留現有招牌,但需經過嚴苛的程序,而當中決定能否保留只有招牌大小及結構安全的考量,以致一些有心保留沿用多年的招牌的店主,雖然一直有好好定期維修保養,面對清拆令及未能於限期內拆除的罰則亦只能拆卸,透過這機制成功保留的招牌少之又少。
我們希望可以參考現有歷史建築有評級機制,讓專業人士以及公眾按招牌的歷史、文化、美學等價值評級,讓值得保留的招牌可得到酌情處理、原址保留。我們剛在展覽『在十七天後』設計了一個招牌評核機制,讓公眾投票決定十七個仍存在街上的招牌的去留,希望透過這展覽收集公眾對招牌的價值和保育的意見,整理後交到有關部門考慮調整政策和條例的可能性。」
霓虹燈招牌見證本地街道變遷
每塊拯救回來的招牌都是城市的見證者,「每次拯救過程都會面對不同的店舖故事、保留招牌不同的難度,曾有一次把招牌包起來時店主哭得停不下來。」難捨難離,招牌承載了滿滿的情感憶記。對於舊情,有人戀眷無限、捨不得放手,亦有人只希望讓它留在過去、不再帶有半點留戀。
「另有一個較少提及的經歷,有一個甚為標誌性的霓虹燈招牌,我們剛好遇到工人正在拆卸,雖然全部霓虹光管已經在拆卸過程中打碎,但在鐵皮招牌被送到回收店前,從工人手上保留到。不過數日後收到店主聯絡,不希望我們保留招牌,只好交回讓承辦商棄置。說實話這是一個十分失望及可惜的結果,但也令我們明白有店主希望招牌隨店舖結束走進歷史不想留下任何痕跡,這些意願我們都需要理解和尊重。」

保留下來後,他們主要以物料分類,「有數個完整的伸出式霓虹燈招牌(在「招牌種子庫」中展出的和昌大押)、有未能完整保留未拆下的霓虹光管及鐵皮字、也有不鏽鋼跟銅等不同金屬的、亞加力膠燈箱及個別招牌字、較舊式的木字及木牌匾等。
比較特別的是九龍城公和荳品廠室內牆上的水泥字,這種招牌字本身為建築物的一部份,要拆下保留難度較高。而店主特別安排承辦水泥字連同背後的牆身完整拆下(仍可看到牆身上的舊式紙皮石飾面)再交由我們保留,由於每塊字的重量達二百至三百公斤,運送及展出的方式都需要詳細計劃,剛好這次尖沙咀建築雙年展的地舖適合展出這組招牌。」單是物料的運用已是一門美學,一個招牌一個世界。
由下而上的霓虹燈設計文化
要竭力保存,只因招牌在他們眼中是獨一無二的景物,「招牌的性質本身介乎於商業實用和設計藝術之間,它的存在空間又介乎於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灰色地帶,實際亦是城市照片內最顯眼、突出、易於分辨的物件,因而不免跟城市歷史、店舖背景、商業文化、社會風氣、人文風景等的街道文化有非常直接的關係。」它是相當有趣的存在,「從表面看來招牌只是個別店家的宣傳途徑,但背後其實蘊含不同價值:有美學上的如招牌字的書法、招牌外形、圖案設計、各種招牌物料的工藝等;也有歷史及文化上的如店舖行業的歷史、紀錄社區發展的歷史、作為地標及尋路/導視的作用等。 」一個招牌所訴說的又豈止於一家店的故事?每個細節都值得我們好好細味探究。

隨之再藉由建築師的角度補充:「建築以及街道/城市景觀一般都是透過由上而下的過程設計,招牌卻相反,一般在建築落成後才由各間店舖建造(其實在現行的招牌規管法律實施前,建築師較少參與招牌建造),這些由下而上的設計將狹窄的街道變成獨特、豐富的城市景觀。
招牌在建築上的實際連繫也隨時代而演變:由以往水磨石及水泥招牌字直接安裝在建築外牆上,到垂直於外牆的各種伸出式招牌,推演至後來玻璃幕牆建築不容許後加招牌而出現安裝在室內、玻璃後面的霓虹燈或燈箱招牌。」在他們眼中,香港的美學就藏於大街小巷之中。「招牌景觀並不是某一方面大力打造下的產物,香港的美體現於由下而上的集體創造力,有著透過自然更替去蕪存菁過程,以及日積月累下而成的新舊交錯和多元性。」